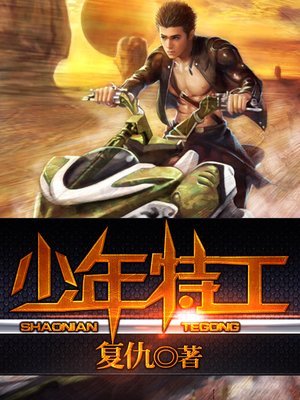外面冰天雪地,寒封萬裡。車内卻是溫暖如春,花香滿室,透着朝氣蓬勃的暖暖春意。
馬車内四角放置無煙火爐,潔白羊絨鋪地,中間放着一張精緻的矮腳青玉案。
案上有新鮮的水果。
杯中有溫熱的美酒。
紅泥小爐,溫火綿綿。氣氛惬意安甯,對面貌若天人一樣的少年含笑望着打着哆嗦的步天音。然而步天音内心雖然緊張,但她實在耐不住腳寒,還是用顫抖的手将自己濕哒哒的鞋子褪下來放在車門角落裡,猶豫了一下,兩下将襪子也脫了下來,赤腳放在羊絨地毯上。她根本不在意什麼男女有别。這地毯果然和她想的一樣,是暖的,和看起來一樣溫暖。她舒服的歎了一口氣,睨了眼對面一身風華的少年。
他看起來不過十六七歲的模樣,盤膝而坐,卻難掩修長的身形。穿着月白色的絨袍,臉色微微發白,容貌卻姣麗如女子,恰好那雙傾世絕豔的美眸夾雜着點點訝然,卻也是平靜的凝望着她。
雲長歌伸手,取了爐上溫着的酒杯遞給她,唇邊溫潤的笑意打破了雪夜的沉默。步天音本不想去接,但她實在是眼饞那看起來清醇聞起來甜香的美酒,伸手接過,不小心碰到了他的指尖,隻覺得溫潤濕意,她的心尖顫了顫,垂首笑道:“多謝……好心的公子。”她不知道他的身份,姓氏,隻好用了這麼個稱呼。她俯首輕嗅酒香,卻沒有注意到,她說這話的時候,對面的少年眼中似有一瞬花開。
她淺淺嘗了一口,隻覺得百感交集,滋味美得讓她無法形容,有蜜汁、果漿、花液的甜,也有酒的冽,暖意順眼喉嚨一路滑向胃裡,她的身子終于有了一絲暖意。雲長歌将身側疊得整齊的小毯遞給她,步天音也不客氣,拿過裹住自己發冷的雙腳,吸了吸鼻子,開門見山問道:“你認識我?”
雲長歌笑而不語,又遞給她一個套着護手的手爐,步天音咬着唇接過,隻覺得眼前之人的笑意直達眼底,卻又深不可測。她不敢再去看他,将目光放在了角落的一個無煙火爐上。不知道為什麼,她覺得這個美人很危險,但是他似乎并不會傷害她。
“我們不認識。”雲長歌突然開口。
步天音一愣,他不認識她?既然不認識那他的仆人還能叫出她的姓氏,邀請她去見他?如果不認識,他何必來見她?步天音偷瞄他一眼,想看看他是不是在說謊,可他的表情一如方才的隐含溫潤笑意,俊美的臉龐上除了笑什麼也看不到。“你是步家的嫡長女。”
對上他的目光,步天音心尖一陣抽緊,忽然明白他們是真的不認識,然而他卻認得她的原因。
确切的說,他不是認識她,而是認識她臉上的這塊“胎記”。步家嫡長女廢柴無顔天下皆知,這塊黑炭似的胎記也是她獨一無二絕無僅有的标識。他不用認識她,隻需知道一個臉上有這樣無雙胎記的人,就是她步天音即可。
面對如此天人,步天音并不覺得自己顔醜而心有羞愧。處于被動從來不是她的風格,但面前這個人,身上并沒有任何危險的氣息,相反卻是待她如舊友,以車避寒,以酒暖身。倒讓她一時不知措施,揣摩不到他的意圖。
“你在懷疑我,卻找不到懷疑的理由。”雲長歌笑着說,“我并非以貌取人之人,但步家的大小姐,似乎和傳說中不太一樣。”
“是啊,我比傳說中更不濟,更傻,更廢柴,更醜陋,所以不知道公子為何要救這樣的一個我?”
“君子有德,怎忍見一個薄弱女子獨自彷徨雪夜而不顧?”雲長歌對她舉杯,“利州名酒雨花青,千金難得,天下僅有兩壇。小步何不與我共飲?”
步天音沒來由的一笑,小步?這個人,看起來優雅尊貴,喚起人來可真是随意啊。她亦不作推辭,第二杯一飲而盡。這次的味道和方才的不太一樣,似乎酒的醇香大過甜香,她渾身一抖,暖意從胃裡向四肢蔓延開來。
雲長歌笑道:“雨花青,初杯清甜,二杯身暖,三杯麼……”
“會如何?”步天音好奇的追問。
雲長歌笑意更濃,雙眸明亮如星月:“你可以一試。”
步天音撇撇嘴,單手把玩空了的酒杯,覺得眼前似乎有些不甚清明,腦子發沉,已有醉意。想來這第三杯要是灌下去,她非死即傷了,這個人也真是壞,明明在害人,還一派笑如春風的樣子。
雲長歌望着步天音的目光因酒意而變得深邃,“你有心事。”
“人活世上,誰還沒個心事?”
“你站在雪地裡茫然,是要去哪裡?”
“賭坊。”步天音自知名聲不好,也沒有打算隐瞞。如果這個人能給她指明一下賭坊怎麼去,最好能駕車送她過去,那麼她,不勝感激。這人看着就聰明,這些話不用點明說出來,他就會懂。
雲長歌笑道:“去賭坊的人無非有兩種,一是去賭,二是去尋人。”
步天音放松的靠在車壁上,雙目微合,卸下心裡最後那一絲防備,懶洋洋的聲音裡略帶倦意回答他:“我缺錢。”
“京都最大的賭坊是東平堂,離這裡尚有半個時辰的路程,你可要去?”
“你打算送我麼?”
“小步開口,豈有不送之理?”
“那我去。”步天音倏然睜開眼,眼角雖然含着三分醉意,但那雙墨色瞳孔卻依舊清明如斯。
雲長歌吩咐外面道:“雲楚,去東平堂。”
雲楚應下,手中長鞭一揮,掉轉馬頭,向着平坦的大路駛去。
“多謝。”步天音向他道謝。
雲長歌微微一笑:“東平堂的規矩,身上沒有一千兩底金的人,是進不去的。”
“什麼?!”步天音猛地坐直了身子,蓋着腳的棉毯也被她踢開來,雲長歌看了眼她裸露在空氣中的潔白玉足,眸中笑意漸濃。步天音卻沒有注意到這些細節,她一心在想自己出來是臨時決定的,也根本就沒有帶錢。本打算拿身上這些耳環、玉镯首飾抵現的,可這幾樣東西,哪裡值得上一千兩?
“能進東平堂一樓的,都是城中數一數二的賭徒;二樓更不用說,賭齡至少十年以上。即使小步你去了,也不一定會赢……”雲長歌循循善誘,他的聲音輕輕,淡的像林間拂過的風,不似男子的低沉,也不似女子的清婉,音線獨特卻十分好聽。“何況夜色深重,你一個孤身女子……”
步天音不耐的打斷他的輕聲細語:“那你說怎麼辦?我既不能進去,進去了也不一定會赢。你明明知道還要送我去?我缺錢缺到快死了,難道你要借給我嗎?!”
雲長歌勾唇一笑:“好。我借。”